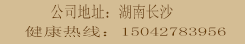![]() 当前位置: 翠鸟 > 翠鸟的天敌 > 深度柴静面对他,我土崩瓦解hell
当前位置: 翠鸟 > 翠鸟的天敌 > 深度柴静面对他,我土崩瓦解hell

![]() 当前位置: 翠鸟 > 翠鸟的天敌 > 深度柴静面对他,我土崩瓦解hell
当前位置: 翠鸟 > 翠鸟的天敌 > 深度柴静面对他,我土崩瓦解hell
?MBAClub,分享传递价值
秘书;
投稿邮箱:post
MBAClub.cn合作邮箱:Cooperate
MBAClub.cn阅读引语
一个在中国广西偏僻山村一呆十年的德国人,进行他所热爱的支教,对象是中国乡村留守儿童,这个热爱与儿童在一起的德国人所实践的教育理念,震惊当下的中国人,令他们充满了不解。柴静不止一次采访他, 次采访后就觉得自己“崩溃”了……
这位德国中年男人无形中成为文青范央视女主持柴静的精神导师。乃至卢安克不得不告别他所热爱的地方和事业时,柴静再次赶过去采访,那一期题为《告别卢安克》的“看见”,始终充满别样的情绪……除了“看见”,好报还挑选了三篇文字素材,让你从不同侧面了解卢安克这样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传说。
这个传说在年的某一天中止,之后,卢安克去了越南,近况如何,很多中国网友关心。零星的网络资料显示:后来他又从越南回到中国,继续支教。但我们无法确证这一消息。
转自:檀道
《告别卢安克》,年“看见”
卢安克·第1篇
我不想感动中国
据《环球》杂志
写于年
在村民眼中,他是一个不吃肉、不喝酒,给学生们上课不用课本,也不要报酬的怪人;在孩子们眼中,他是 的朋友、老师,是可以一起爬树、在泥里打滚的玩伴;在许多人看来,卢安克就像白求恩一样,是能够感动中国的“洋雷锋”,是很多人的偶像;在他自己看来,他与其他人一样普通,只是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……他就是卢安克,一个在中国广西山区义务支教10年的德国志愿者。
山里来了个“洋雷锋”
年7月,广西东兰县坡拉村林广屯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。他在村里以每月10元的价格租了房子开办学校,给当地失学的孩子上课。当时的林广屯不通电话,也不通公路,当地人大多只会讲壮族方言。人们觉得这个外国人真是一个怪人,不好好呆在自己的国家,却跑到中国农村来给学生上课,还不要工资。
几天后,村民知道了这个外国怪人名叫卢安克,是德国人,不吃肉、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赌博。当地人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外国人会自愿到山里给孩子们上课,并且不要钱。
在村民眼中,德国怪人卢安克就是洋雷锋,是来帮中国人搞教育的,老人和小孩都亲切地叫他“卢老师”或者“老卢”。
做学生身边的大人
孩子们把卢安克当作最值得信任的玩伴,而卢安克也是最了解山里孩子的人。卢安克和孩子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爬树、挖泥鳅、在泥地里打滚。白天,卢安克与学生一起去放牛,去干农活;晚上,孩子们在看电视剧,而他则在一边翻译他的书。卢安克与孩子们的关系很亲密,不少孩子会爬在卢安克身上介绍:“他是卢安克,我们都叫他老卢,老卢就是我爸爸。”
卢安克还是孩子们 的老师。“世界上真的有鬼吗”、“男人和女人是怎么回事”,是孩子们问得最多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如果问家里的大人,孩子可能会被骂一顿,而当孩子向卢安克提出这些问题时,他们会得到一个很真诚的答案。
记者问:“关于鬼的问题,你怎么跟学生解释?”卢安克说:“我会告诉他们,我没有见过鬼。有学生说,村里有人看到鬼后就病死了。我就告诉他们,是这个人病了,思想出现了幻觉,才会见到鬼。不是鬼把人害死了,是这个人本来身体就不好才死的。”
记者又问:“关于性的话题呢?”卢安克:“中国的大人一般不愿意和孩子谈性的话题。事实上,孩子愿意提出来,表示他已经知道了一些信息。只要大人愿意去了解孩子所知道的东西,孩子就会很满足,也就不会再问下去了。”
对于即将到来的寒假和春节,卢安克依然会像之前的假期一样到学生家里过。他说:“我会每天去一个学生家,与他们生活,轮流做他们身边的大人。”
这辈子已经交给了山里的孩子
最令卢安克感到不安的是,很多女孩子因为看了媒体报道而声称爱上了他。对于“粉丝”的追逐,卢安克说:“她们说要到学校来找我,嫁给我,有的人甚至说要离了婚来嫁给我,这让我很担心。我想是时候告诉大家我已经有未婚妻了。”卢安克的未婚妻也是一名志愿者,她爱山里的孩子,学校的孩子们也很喜欢她。
得知卢安克有了未婚妻后,板烈村村民的心情忽然变得复杂起来———一方面,他们希望卢安克能早点结婚,因为在农村,男人都要结婚;另外一方面,他们又担心卢安克结婚后会离开板烈,离开山里的孩子。
在交谈中,卢安克多次提到自己就是板烈村的一个村民,就算他离开学校,也是暂时的。他说:“这里有我的学生,他们需要我,所以我还会回到板烈的。”这个学期结束后,卢安克计划去广州看看。学生听说后都问他:“那你还会回来吗?”得到卢安克肯定的回答后,孩子们顿时欢呼起来:“卢老师不走!他还会回来!”卢安克说自己已经把这辈子交给了山里的孩子,“我们的命是在一起的,无论怎样我都会回来”。
对话卢安克:我不想感动中国
“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”
在中国山村义务支教10年,躲记者成为卢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每当有记者来采访,他就会远远地躲到学生家里,等记者走了,再回到学校。他说:“媒体会把我塑造成名人,我只想做好我的事,我不想出名,做名人只会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。”
记者:“你十年来都在躲记者,去年年底为何会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?”
卢安克:“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过一句话,大体意思是‘如果你隐藏着自己,不敢让别人看到你如何做着自己所喜欢的事,别人就会认为,他们也不能做到。但如果你让他们看见,这就等于允许他们像你一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,就等于解放了他们的愿望。这不是说让他们做跟你一样的事,而是说让每一个人做最适合自己的、自己所愿意的事’。我被这句话感动了,所以我 次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。”
记者:“节目一播出,很多人都被你感动了。”
卢安克:“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。年,有人推荐我参加感动中国人物评选,我吓坏了,赶紧给评选委员会写信,让他们别选我。我不想感动中国,只能是中国感动我。”
“我很普通,不想做偶像”
记者:“很多人钦佩你,甚至崇拜你。”
卢安克:“那是他们的感觉,我很普通,不想做偶像。很多人是通过媒体报道了解到我的,那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我。一个人认为别人做的事是对的,也是应该去做的,但自己做不到或者不愿去做,他就只好钦佩或者崇拜。”
记者:“也有人认为你的工作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教育。”
卢安克:“我并不想改变中国的教育,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,我不该干涉。”
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,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做的。
卢安克·第2篇
暂别卢安克
据央视《看见》编导范铭博客
写于年,《告别卢安克》制作后。好报略有删节
每次去板烈村都要从北京飞三个半小时到南宁,再坐四个半小时的山路到东兰县,从东兰县再颠簸一个小时,才进到村里。三年了,一样的路线,一样的山色。不一样的是,那个说自己“命在这里,离开就没有命了”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,写信给柴静说,他很快将不得不离开中国了。
一.“不是征服,而是承受”
见到他时,他穿着超大的篮球跨栏背心,一样消瘦,跟三年前的冬天一样光着脚,一见面,还是基督一般的微笑,被问到“你好吗”的时候,回答“也好,也不好”。见面的最初,谁都没有谈及离开的话题,似乎谁也不忍心问。
我们跟他去一个叫小罗的留守儿童家里家访,曲曲绕绕的山路,深一脚浅一脚,到的时候已经傍晚了。我们在商量先拍室内的纪实还是先采访,卢安克在院子里,对着天边的落霞, 次对我们的拍摄提出要求:“先拍外面吧,晚霞多美啊。”摄像们当时已经在屋里架好了机器,我们说可以改天再专门找地方拍空镜,他坚持说,“小罗家的这个角度,能看到板烈 的景色,再不拍,天就要黑了。”
后来的几次采访也是如此,很多场景是他自己选择,比如他希望坐在他给孩子们拍电视剧的半山腰的大石头平台上采访,那里空旷,视野舒展,能俯瞰到板烈小学和周围的梯田与村庄。
他也会主动地告诉我们,爬到学校屋顶上能拍到什么,哪个山头的哪片树林后面又能拍到什么,去哪里掏螃蟹,去哪里挖蚯蚓??他在这里陪伴留守儿童已经十多年,漫山遍野都是他的步子,一草一木都是他的乐趣,当他一言不发地望着大山发呆时,他仿佛整个人也都沉浸在与这片土地 的相处中。在接受采访的那几天,他隔断了自己 与外界通讯的方式——邮件。他说他想安静地度过这几天,他太紧张了,紧张到都不敢看邮件,怕家人又写信催他回去。
柴静说,这是她见到的卢安克,最“失稳”的一次。
柴静:你已经为留守儿童做了很多了,你可以有机会去过你个人的生活。
卢安克:如果我觉得我欠他们什么,就会这么说,我不是因为觉得欠他们什么,我是喜欢。
柴静:如果按你自己的意愿选择,你希望怎样生活?
卢安克:就喜欢继续留在这里。
他劈着木头生火,柴安静地陪他坐着,两个人都不说话,只有木柴烧裂的咔嚓声和缓缓蔓延开的小火星子,直到卢安克缓缓说,“(离开)是我老婆的选择”。
当年的卢安克“不喝酒、不吃肉、不谈恋爱”,因为他心中,有“比这些更大的乐趣”。但一年多前,他与曾经同在山区服务多年的女志愿者结婚,而妻子已经到了渴望安定生活的年纪,她对未来并无太多物质的需求,但担心卢的理想主义会受他人利用,希望他能离开板烈,并帮他在杭州一个手机企业找了一份正常工作。卢不愿意去那个手机企业,又不忍违拗妻子,只能选择离开。而他的签证即将到期,如果结束支教又没有新工作,他也会同时失去留在中国的合法身份。
他说他的处境,就跟他和孩子们一起创作和拍摄的电视剧《心镜》中的主角容承一样。容承的意思,大约便是“容忍和承受”。这个主人公没有任何超能力,他的能力就在于能够接受一切的压力、攻击、羞辱、困境,没有所求,没有目的,他的心灵干净到无法被敌人持有的“心镜”识破,无法被反射和看穿,也无法被击倒。他的力量,不来自于征服,而来自于承受。
卢安克不愿意离开,他说一想起要走,他的心“象死去一样可怕”,但他依然决定接受将要到来的命运和家庭的责任。他曾经说过:人更大的能力是“有能力却不使用。”但此时,他也不得不因此而承受痛苦。他问柴静,“我该怎么办?”
二.“不,他们需要真”
在小罗家,小罗兴冲冲地要给我们做晚饭。剥扁豆,淘米、摘小西红柿……各种忙碌。
“能烧给我们这么多人吃?”“没问题。”
电饭煲的旋钮已经生锈了,他用一把大钳子咬着开关拧开,把米倒入。炒菜时也很老道,炒、翻、转、拌、挑,一点不拖泥,反手动作也极为熟练,柴静问他谁教的,他说烧着烧着自然就会了,火光照过来,手背上却俨然有一尺长的红色烫疤。
因为在拍摄,摄制人员一口都没吃,小罗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,端着饭要递给我们,我们不吃,他也不吃,完全是做主人的心态,操心命。我们开始不好意思,硬要劝他吃,卢安克说不用劝,这是孩子待客的习惯和心意。
结束拍摄后,因为他只做了一碗扁豆炒小西红柿,量根本不够,我们便转去另一个老乡家吃饭。事后我有点后悔,问卢安克,孩子忙了半天,我是不是应该象征性地吃一口,并且夸赞小罗两句?我说,“我小时候要是做菜,每个人都必须说好”。卢安克说“他应该不会在意的”。我说“孩子们不是都需要夸吗?”,他淡淡说,“不,他们需要真。”
他的眼里有让人失语的蓝,让我看到自己出于善意而生的“伪”,我觉得他的眼睛就像是一面“心镜”。
他比谁都更了解这些留守的儿童,了解他们内心的孤独和敏感,了解他们不需要成人世界的应酬和客套。就像他在《农村支教指南》里写的: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看到,“有一个人,他在作为真实的自己。在陪伴着我的时候,他忘掉了所有的想法,仅仅保留着真实的自己。”
三.“思考带来痛苦,行动才有用”
采访时,我们把班上一个平时威风八面,呼来闯去的一个“老大”弄哭了。因为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,他过于紧张,回答不出,然后突然就肚子痛,满头冒汗,眼里全是泪。
卢安克说,是因为这个孩子真的在“思考”,真的希望回答我们的问题,真的“在乎”,所以压力太大。回到宿舍,卢说孩子们都在讨论要怎么折腾我们,比如让我们去爬后面的大山,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很累,而他们觉得“思考很累”,我们让他们“累死”,他们也想让我们“累死”。
他说,在农村,人的身体需要劳动,需要行动,而在行动的同时去思考对野惯了的山里孩子来说是很难受的,所以不如让他们通过行动来完成任务,先行动,后感受,再理解。从行为到思维,再从思维到行为。只有拥有“感受”,才能从内心深处理解。
临走前的一天,编导蚂蚁和摄像纪可成扛着机器,走了来回整整三个小时的山路,跟“老大”一起,翻山越岭,淋雨、晒太阳,捉鱼,一直到日落西山。也许,只有走过一座山,才能了解山;只有陪一个人走过漫长的路,才能走进一个人的心里。
卢安克说,不管是成人,还是孩子,真正的教育是“自己教育自己”,“知道”和“体会到”是两码事。
他说,许多志愿者来了,总是喜欢让孩子宣泄内心痛苦,让他们意识到城乡的差别,让他们盼望去大城市,渴望脱离农村,为了这个目标再去努力学习,他们还喜欢把城里的一套拿到农村来,搞竞争,搞比赛,弄得农村的老师“恨不得心脏病都出来了”。一定要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感到不满。但改变不了其实反而成为痛苦。
柴静:但有人会觉得说,如果为了孩子更有出息,让他们痛苦一点,意识到自己对现实的不满,也许也是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,不是吗?
卢安克:那去了城市也可能会痛苦。
柴静:他们会问你,难道你的主张就是什么都不做吗?不鼓励他们拿外界跟自己的生活做比较,也不鼓励他们?
卢安克:我觉得还是如果他们能学会创建自己的东西,他们到城市的时候,也不用觉得别人那么有钱,我没有,我被抛弃。他可以自己创建,他不需要逃。
卢安克说,他们从小没有家长,没有家,所以更需要一个权威,创作可以成为他们的权威,可以给他们归属。
四.“急急不成事”
对孩子的群体采访在谷堆上进行,孩子们几乎没有一刻安静得下来,永远在欢腾地打来打去,男生都七横八歪靠在卢安克身边,女生一近前就大喊“男女授受不亲”。女生们则坐在另侧,在麦堆里挑拣麦秆,把表皮剥开,露出里面嫩嫩的象牙白色的小管子,放在嘴边做成小哨子,一吐气就能吹出呜呜的声音,她们做了几个,送给柴静,看谁吹得更响。
“创作就是玩,玩就是创作”。卢安克跟孩子们拍的剧几乎算不上一个电视剧,主角容承的扮演者更换了十几次,由学生自告奋勇,大家投票,轮番扮演,演的过程中孩子们也是打打闹闹,完全谈不上表演,只是把属于自己的台词说出来,经常卡壳,经常笑场,但就是这个剧刻成的光碟,被孩子们视作童年的珍宝。
卢安克说他不需要他们懂得具体台词的含义,人生有很多事是先做了,未来才会明白。此时一个一直很皮、没说过什么正经话的孩子突然脱口而出说,“不要急,不要急,急急不成事。”
从卢安克支教的轨迹表象看来,他似乎逐步在往后退。最早他在县初中教主课英语,因为适应不了应试教育,于是离开;之后他教不识字的青年修路、画地图,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,但发现他们没有应有的感受力和创造力;再之后,他从小学的孩子教起,教音乐、美术等副课,但孩子长大了,读到初中,还是会有大量孩子辍学打工、消失进茫茫的人海;再之后他完全放弃对结果的设计,放下期待,陪伴孩子,默默做着人之为人的最不显见却最本质的心灵建设。
我们没有去刻意搜集或列举卢安克给学生带来的实在的改变,因为人的心灵只有在未来漫长的人生中才能逐渐显出力量。我们只是在我们采访中接触到的几个孩子身上体察到细微的痕迹,比如他们眼里的光芒,比如他们对未来的想像。
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学生有期待、愿望或者“他们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人”这种想法,我们这种想法就会像一面隔墙一样站在我们和学生的之间。只要我们放弃对“什么是好的”这种想法,我们就会发现:什么都行,学生什么都能做到。那是因为放弃之后,我们就无偏见地去观察,而通过观察,我们能找到 他们的角度。——卢安克《农村支教指南》
跟卢安克一起创作电视剧的潘老师,作为国家财政特招的特岗老师定点在乡村当老师,三年后,他本可以选择离开,但在跟卢安克一起工作后,他说他会留下来,因为这里有“创作的自由”。
柴静问他说,“可是在外人看来,会觉得说这样的创作又不被外界的人看到,只有几个小孩子,拿着光碟在寂寞的大山里放,那它对你来说能有那么大的含意吗,有那么重要吗?”潘老师回答说,“里面有一种别人看不到的东西”。
五.“没有期待的日子”
一个曾经申请过《静观英伦》实习生的留学德国赵赫同学前段时间给我写信,写到一个白发苍苍的德国教授的故事。
“他曾在上海参与创建了一家生物学研究所,他的学生都叫他“老爷爷”。在他和一些中国教授一起为研究所确定发展目标的时候,中国教授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:“努力成为世界前十名的XX领域的研究所。”‘老爷爷’在演讲时说的很有意思,他说我非常不赞同这个说法,因为我们是世界上 的一个这个领域的研究所,哪里来的前十之说。这是他的一个玩笑。他说,我的观点是,让我们的研究所成为Aplacewherescienceisdrivenbycuriosity.”(科学被好奇心驱动之地)
而这正是我前段时间自我剖析时思考的问题——我和身边的许多同学努力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和别人的比较。我们看到对手努力了,就会紧张起来,也要加紧努力。我们看到自己的排名下降了,意识到要更加用功,只有赢了,才更有自信。
我们无时无刻有意无意的生活在比较之中,我们必须得通过比较来体现 。我们那么北京看白癜风什么医院好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科学大讲堂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cuiniaoa.com/hgfz/4433.html